【内容提要】 “惠棟校宋本”這一表述,肇始於阮元《禮記注疏校勘記序》。這一表述,不僅充斥于阮元的《禮記注疏校勘記》,而且成爲近二百年來令中外《禮記》學界備受關注而又備受困惑的一個熱門議題。何者?據說,這個“惠棟校宋本”解決了數以萬計的校勘問題,神通如此廣大,能不備受關注嗎?而當人們較起真來,試圖核查這數以萬計的校勘記在“惠棟校宋本”中的實際存在情況時,卻發現與“宋本”相合者只是少數,不合者是大多數。遇到這種情況,能不備受困惑嗎?問題出在哪裡呢?本文認爲,問題的癥結在於“惠棟校宋本”是個錯誤的表述。正確的表述應是“惠棟校毛本”。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當我們改正了錯誤的表述,輔之以陳垣校勘四法的歸類,再來核查這數以萬計的校勘記在“惠棟校毛本”中的實際存在情況時,將會是怡然理順,合若符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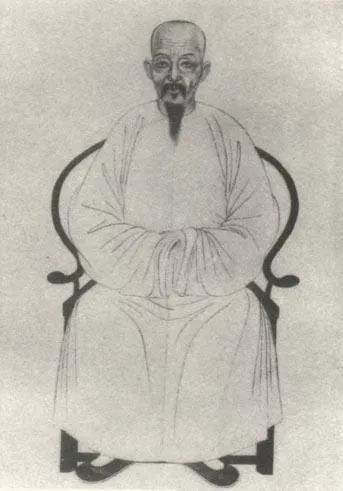
惠棟 像
事情從頭說起。乾隆十四年(1749),惠棟利用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校勘了毛本《禮記注疏》,很有收穫,就在此八行本書後寫了一則跋語:
拙菴行人購得宋槧《禮記正義》示余。余案《唐萟文志》,書凡七十卷,此本卷次正同。字體倣石經,蓋北宋本也。先是,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法周、秦遺意,與經、注別行。宋以來始有合刻。南宋後又以陸德明所撰《釋文》增入,謂之《附釋音禮記注疏》,編爲六十三卷。監版及毛氏所刻,皆是本也。歲久脫爛,悉仍其闕。今以北宋本校毛本,訛字四千七百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羨文九百七十有一。校讐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犁然備具,爲之稱快。唐人疏義,推孔、賈二君。第《易》用王弼,《書》用僞孔氏,二書皆不足傳。至如《詩》、《春秋左氏》、《三禮》,則旁采兩漢、南北諸儒之說,學有師承,文有根柢,古義之不盡亡,二君之力也。今監板、毛氏所刻諸經,頗稱完善,唯《禮記》闕誤獨多。拙菴適得此書,可謂稀世之寶矣。拙菴家世藏書,嗣君博士企晉嘗許余造璜川書屋,盡讀所藏,余病未能。息壤在彼,請俟他日。因校此書,并識於後云。己巳秋日,松崖惠棟。
惠棟在這則按語中,有說錯者,如把此南宋刊八行本誤認爲“北宋本”是也;有讓人大惑不解者,如“四百年來闕誤之書”一句是也。爲了避免行文枝蔓,這些都暫且擱置不提。關鍵的是這幾句話:“今以北宋本校毛本,訛字四千七百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羨文九百七十有一。校讐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犁然備具,爲之稱快。”人們要問的是,這麼巨大的校勘成績,訛字、脫字、闕文、文字異者、羨文,五項相加,凡一萬一千六百六十二字,都是出自“北宋本”嗎?惠棟既沒有明確說是,也沒有明確說不是,給讀者留下遐想的空間。
“惠棟校宋本”這一表述的確立者是阮元。阮元在《禮記注疏校勘記序》中說:“《禮記》七十卷之本,出於吳中之吳泰來家。乾隆間,惠棟用以校汲古閣本,識之云:‘訛字四千七百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羨文九百七十有一,點勘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犁然備具,爲之稱快。’今《記》中所云‘惠棟校宋本’者是也。”惠棟的巨大校勘成績何出,在他自己的的跋語裏還是一本糊塗賬,現在經阮元這麼一說,就基本坐實了:惠棟的全部校勘成果,都裝進了“惠棟校宋本”這個籃子裏了。說得再明白點,就是那一萬一千六百六十二字的校勘成績,都應該歸功於“宋本”。從阮元這一錯誤表述誕生之日起,學術界就進入了多事之秋。
校勘記的命名慣例是根據校勘的對象來命名,不是根據所使用的通校本來命名。以阮元爲例。《清經解》有阮元《宋本< 十三经注疏>倂< 經典釋文>校勘记凡例》一文,請注意,阮元在《十三經注疏》前特地加上“宋本”一詞。爲什麼?其《凡例》第一條解釋說:“《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谷梁傳》、《論語》、《孟子》凡十經,以宋版十行本爲據。”可知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之命名猶循斯例。阮元還有《石經儀禮校勘記》四卷,《儀禮》之前又特地冠以“石經”二字,其用意也不言而喻。據此慣例,阮元所謂之“惠棟校宋本”,其正確表述應是“惠棟校毛本”。這個“毛本”,在阮元生活的時代,既是學者普遍使用之本,又是問題最多亟需校勘之本。知者,阮元《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錄》云:“今各省書坊通行者,唯有汲古閣毛本。此本漫漶,不可識讀。近人修補,更多訛舛。”阮元《宋本< 十三經注疏>並< 經典釋文>校勘記凡例》第三條:“毛本《詩》少《譜序》,《左傳》失刊《後序》。且魯魚亥豕之訛,觸處皆是,棼不可理。今日坊間又將毛本重刊,則訛字又倍之。”阮元之一再指出“毛本漫漶,不可識讀。近人修補,更多訛舛”,“魯魚亥豕之訛,觸處皆是,棼不可理”,不僅可證毛本之亟需校勘,而且可證惠跋所謂“今以北宋本校毛本,訛字四千七百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羨文九百七十有一”云云,乃指惠棟校出毛本之種種錯誤而言,所以下文才有“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犁然備具,爲之稱快”之語。且以毛本爲校勘對象,爲當時風氣所尚,非惠棟一家爲然。知者,盧文弨在《群書拾補》的《周易注疏》下說:“外間通行,唯毛本獨多。故仁和沈萩園廷芳、嘉善浦聲之鏜作《十三經注疏正字》,日本國足利學山井鼎等作《七經孟子考文》,皆據毛本爲說,今亦依之。”然則,一世風氣所尚,惠棟也莫能外,是惠棟校毛本也,非校宋本也,安得謂之“惠棟校宋本”耶?且宋本是“稀世之寶”,何校之有?
阮刻《禮記注疏》于嘉慶二十一年(1816)問世,迄今整二百年,風行于世。而“惠棟校宋本”一語,從其啟用之日起,雖質疑之聲不絕於耳,但由於沒有正本清源,學術界始終處於被阮元錯誤表述牽著鼻子走的狀態,學者只有被動招架之功,沒有主動還手之力。如此曠日持久,不知伊於胡底!
既然“惠棟校宋本”的含義是指那一萬一千六百六十二字的校勘總成績,那麼當人們用八行本去核實這一萬一千六百六十二字的校勘總成績時,應該合若符契才對。而實際情況是,合者固有,不合者更多,於是質疑之聲,此起彼伏。
首先,與阮元同時代的學者盧文弨就發出質疑之聲。例如:
“周禮大濩大武”, 阮校云:“惠棟校宋本‘大濩’上增‘殷曰’二字,‘大武’上增‘周曰’二字。盧文弨云:‘惠棟本依《史記集解》增。’”
吕按:檢視足利本與惠棟校宋本(又稱“潘本”。以將此宋本捐獻給國家者的姓氏命名),“大濩”上皆無“殷曰”二字,“大武”上皆無“周曰”二字。見《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1045葉倒2行,可覆按也。盧文弨就像是安徒生童話《國王的新衣》中的小孩子,說了一句大實話:“惠棟據《史記集解》增。”盧文弨實際上是告訴讀者,惠棟此處的校勘依據並不是宋本,而是南朝宋裴骃《史記集解》。從校勘方法上來說,不是對校,而是他校。在揭示“惠棟校宋本”真面目上,盧文弨可謂先知先覺者。他實際上是在通過這個例子提醒人們,千萬不要把惠棟的巨大校勘成績統統歸功於宋本。按道理,阮元既然在其校勘記中徵引了盧文弨這種揭示真相的大實話,他自己對“惠棟校宋本”這一表述是否嚴謹也應有所反省才是。看來,阮元並沒有任何反省,而是等閒視之。阮元等閒視之事小,我們後人等閒視之則事大。而遺憾的是,恰恰是我們後人並沒有意識到盧文弨的這個提醒,仍然臣服于“惠棟校宋本”這個錯誤的表述,繼續被錯誤的表述牽着鼻子走,一場無謂的曠日持久的質疑還將繼續下去。
爲明余言之不誣,筆者將以以下三大家的質疑爲例予以說明。哪三大家?潘宗周,一也;常盤井賢十,二也;《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編後記》作者,三也。之所以謂之三大家,是因爲這三家對南宋越刊八行本都極其熟稔,如數家珍,且有相關著述,非其他道聽途說者可比。潘宗周,一度是所謂“惠棟校宋本”(後習稱“潘本”)的故主,且著有《禮記正義校勘記》(1928)一書。常盤井賢十,既目睹藏於日本足利學校遺跡圖書館之八行本《禮記正義》(習稱“足利本”),又目睹我國之影潘本與覆潘本《禮記正義》,眼福罕匹,著有《宋本禮記疏校記》(1937)一書。《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編後記》一文之作者,恨不署名,無緣識荆,必是北京大學有識之士,其爲學界貢獻《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一書,功德無量。而《編後記》之作,亦非此君莫能爲也。
潘宗周《禮記正義校勘記附識》云:“檢阮校所引惠校,多與此本不合。惠校實另有北宋本。書中異同之處,與惠合者固多,不合者正不少。”這幾句話是潘氏對“惠棟校宋本”的總體看法。可以看出,潘氏將阮元“惠棟校宋本”的表述是奉若神明的,你看,他對阮校中的任何一條提到“惠棟校宋本”者都嚴加審查,不輕易放過,這不正是臣服于“惠棟校宋本”的精神狀態的寫照嗎?這不正是被阮元錯誤表述牽著鼻子走而不悟的思維方式導致的結果嗎?其用力之勤,令人佩服;而其不知反思,令人惋惜。其“惠校實另有北宋本”的斷語是錯誤的,究其原因,主觀上是他對“惠棟校宋本”的錯誤表述的迷信,客觀上是惠跋的“北宋本”之說有以啟之。其所謂“書中異同之處,與惠合者固多,不合者正不少”,是合乎實際的判斷,遺憾的是未能做進一步的分析:“合者”有何特點,“不合者”有何特點?如果試加分析,則“惠棟校宋本”的真相就有可能浮出水面。
下面讓我們來檢視幾條潘氏《校勘記》中的具體例子。先看潘本與惠棟校宋本合者:
例一:5葉1行:“始皇深惡之”,潘宗周校云:“此本‘始’字缺右上角,‘皇’字誤作‘星’,‘之’字缺。阮校引惠校云:‘宋本“皇”誤“星”,“之”字脫。’則此訛脫之跡,此本亦與惠校本相合,宜可以信爲即惠校本矣。”
呂按:檢視《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5葉下欄1行,潘說信然。足利本沒有訛脫。
例二:惠校所據之宋本卷二缺少第十、第十一兩葉,潘氏《校勘記》云:“十及十一兩葉原缺而係鈔補,據阮校引惠校宋本正缺此兩葉,此亦與惠校本相合之證。”
呂按:檢視《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23葉與24葉下欄,潘說信然。足利本此兩葉不缺。
例三:惠校所據之宋本卷三缺少第二十葉,潘氏《校勘記》云:“二十葉缺,鈔補。阮校引惠校宋本缺,則與此本同。”
呂按:檢視《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52葉下欄,潘說信然。足利本此葉不缺。
再看潘本與惠棟校宋本不合者:
例一:“是決嫌疑者”句,阮校云:“惠棟校宋本‘嫌’下有‘也’字,無‘疑者’二字,是也。衛氏《集說》同。”據此,則此文作“是決嫌也”,與下文“是決疑也”爲對文。今此本不然,則非惠校之宋本。
呂按:今檢足利本及惠棟校宋本,皆作“是決嫌疑者”,並非“嫌”下有“也”字,無“疑者”二字。見《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12葉4行,可覆按也。就此例而言,我們只能說惠校是對的,不能說惠棟校宋本是對的。因爲南宋衛氏《集說》不誤,惠棟極有可能是採用他校法與本校法得出的校勘結論。早於惠棟三年的殿本《禮記注疏》卷一考證已經得出與惠校相同的結論,且言之更詳:臣召南按:“‘是决嫌疑者’,當作‘是决嫌也’,與下文‘是决疑也’相對。陳澔《集説》引此條甚明,可知宋以前之本不誤。”齊召南也是根據他校與本校得出的校勘結論,惠棟未必能夠看到齊召南之考證,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例二 :“前疾”,阮校引惠校云:“《詩疏》及《論語》邢疏皆作‘前矦’,此獨作‘前疾’,非也。”按:此爲惠氏校正文字,不據宋本,而據《詩疏》、《論語疏》定之。“立當前疾”,見《周禮·大行人》,賈疏已莫能辨正,惠士奇《禮說》乃據《詩》及《論語疏》,參合鄭注,定“疾”字爲“矦”字之誤。定宇本其家學爲說,原文具詳《禮說》,文繁不具錄。定宇《九經古義》亦詳之。
呂按:檢視《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37葉1行,足利本與潘本皆作“疾”,不作“矦”,誠如潘氏《校勘記》所說。而潘氏“此爲惠氏校正文字,不據宋本,而據《詩疏》、《論語疏》定之”云云,可謂識破本相,一針見血之語。惠棟此例的校勘結論,得之於他校。
例三:“以其在下總會之處”,阮校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下’作‘上’。”而潘宗周《禮記正義校勘記》云:“此非惠棟校宋本,但必當從惠。”
呂按:檢視《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1187葉7行,字皆作“下”,不作“上”,與惠棟校宋本不同,故潘氏云“此非惠棟校宋本”。而潘氏又云“但必當從惠”者,是其校勘結論也。筆者推測,惠棟此處是根據上下文,運用本校法得出的校勘結論。知者,此句上文云“上緣謂之會”也。
至此,我們可以爲潘氏之二本“相合”與“不相合”做一小結:凡“相合”者,必是惠棟對校宋本得出的校勘結論;凡“不相合”者,必是惠棟採用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得出的校勘結論。
下面讓我們看看日本學者常盤井賢十對“惠棟校宋本”的看法。常盤井賢十《宋紹熙版禮記正義略說——比較足利本與潘氏本》云:“檢阮元《校勘記》所引惠棟校宋本,覈之潘氏藏宋本,往往有不符之處。試舉其二三。如惠棟校宋本每卷末題‘禮記正義卷第幾終’,而潘氏本僅作‘禮記正義卷第幾’,無‘終’字。卷一‘夫禮者’節正義‘是決嫌疑者’,《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嫌”下有“也”字,無“疑者”二字是也。’而潘氏本同於閩、監、毛本,非如惠棟校宋本。卷三‘名子’節正義‘各依文解之’,《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依”作“隨”。’而潘氏本仍作‘依’;‘凡進食之禮’節正義‘末邊際置右右’,《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作“左右”是也。’而潘氏本仍作‘右右’。然當惠棟對校時,或阮元《校勘記》引惠校時,皆容有筆誤,則不得因此等小異,遽斷潘氏本非惠氏所據。其實,潘氏本卷二第十、第十一葉,卷三第二十葉,卷十九第十八葉,卷二十八第八葉等皆補抄,而《校勘記》載惠氏云:‘某至某字止,宋本闕。’所言缺葉與潘氏本完全符合,是認定潘氏本即惠氏所校宋本最有利之證據。”
上述這一段話反映了常盤井賢十對阮元“惠棟校宋本”的總體認識,讓我們試着加以分析。首先,常盤井開宗明義就說:“檢阮元《校勘記》所引惠棟校宋本,覈之潘氏藏宋本,往往有不符之處。”竊以爲,這與潘宗周《禮記正義校勘記附識》開宗明義所說“檢阮校所引惠校,多與此本不合”如出一轍。因此,我們有理由說,常盤井與潘宗周一樣,也是將阮元“惠棟校宋本”的表述奉若神明,同樣是被阮元錯誤表述牽著鼻子走而不悟的思維方式。常盤井比潘宗周進步的是,儘管他發現二者“往往有不符之處”,但能從大局着眼,不否定潘氏本即惠棟校宋本。至於常盤井爲“往往有不符之處”所做的解釋:“然當惠棟對校時,或阮元《校勘記》引惠校時,皆容有筆誤,則不得因此等小異,遽斷潘氏本非惠氏所據。”竊以爲是皮相之論。謂予不信,請將常盤井所據四例試加分析。
第一例:“惠棟校宋本每卷末題‘禮記正義卷第幾終’,而潘氏本僅作‘禮記正義卷第幾’,無‘終’字。”
呂按:常盤井此例,潘宗周《校勘記》已先言之:“十三葉三行:禮記正義卷第一,阮校云:‘惠棟校宋本此節以上爲第一卷,卷末標“禮記正義卷第一終”。’今此本無‘終’字,可知非惠校本。”今按:檢視《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13葉3行,足利本、潘本皆無“終”字。此例之所以與潘本不符,蓋惠棟違背對校法規則,以意妄補,非筆誤也。
第二例:“卷一‘夫禮者’節正義‘是決嫌疑者’,《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嫌”下有“也”字,無“疑者”二字,是也。’而潘氏本同於閩、監、毛本,非如惠棟校宋本。”
吕按:常盤井此例,潘宗周《校勘記》已先言之。上文余已有辨,此不赘。此例之所以與潘本不符,蓋由於惠棟使用的校勘方法是他校與本校,並非是與宋本對校。此與筆誤毫不相涉。
第三例:“卷三‘名子’節正義‘各依文解之’,《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依”作“隨”。’而潘氏本仍作‘依’。”
吕按:阮元這條校勘記,只見于《清經解》本,不見於中華書局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這條校勘記,出得讓人莫名其妙。何者?阮元在與此條校勘記緊接着的前一條校勘記中說:“名子者節,惠棟云:‘常語之中’至後葉注‘無大小皆相名’‘相’字止,宋本闕。”說白了,就是缺了一整葉。檢視《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52葉,可知足利本此葉不闕,作“各隨文解之”;而潘本原闕此葉,據毛本鈔補,作“各依文解之”。阮元既知惠棟校宋本闕此葉,復出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依’作‘隨’”,豈非無中生有?茍或惠棟本人既出校說明宋本闕此葉,復出“惠棟校宋本‘依’作‘隨’”之校,則亦無中生有,讓人百思不得其解!潘宗周《校勘記》亦指出:“二十葉缺,鈔補。”此例之所以與潘本不符,蓋由於惠校或阮校無中生有,無事生非。
無獨有偶,近日讀王鍔《八行本< 禮記正義>研究》,王先生在筆者之前就發現了數例無中生有的校勘記。阮元在《學記》篇出了一條校勘記:“大學之法節,惠棟校此節疏‘不越其節分而教之’,‘分’字起,至‘自是學者之常理’‘自’字止,宋本闕。”實際上就是潘氏八行本闕一葉,見《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1005葉下欄。
奇怪的是,就在這面闕葉的文字中,竟有六處“惠棟校宋本”出現在阮校中,它們是:
①“此朋友琢磨之益,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磨’作‘摩’。”
②“廢滅,惠棟校宋本如此,閩本二字闕,監、毛本作‘廢弛’。”
③“發然至廢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④“若情欲既發,惠棟校宋本作‘若’,此本‘若’誤‘則’,閩、監、毛本同。”
⑤“終難成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終’上有‘而’字。”
⑥“獨學謂獨自習學,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習學’作‘學習’。”
對此種現象,王鍔說:“惠校明言宋八行本闕一葉,又有校勘記六條,原因不明。”
第四例:“‘凡進食之禮’節正義‘末邊際置右右’,《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作“左右”是也。’而潘氏本仍作‘右右’。”
呂按:常盤井此例,潘宗周《校勘記》亦先言之:“‘右右’,阮本同。阮校引惠校宋本作‘左右’是也。(潘氏)按:據此可見,此本不同惠校本。但惠校宋本殊誤,阮反以爲是,則阮之誤也。經言‘右末’,故疏釋之云:‘末,邊際。置右,右手取際,擘之便也。’‘置右’自爲句,‘右手’字屬下句。文義甚明,安得作‘置左’?”今按:潘校是也。足利本與潘本均作“右右”。見《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57葉8行,可覆按也。惠校誤之在前,阮校盲從在後。此例屬於對校,對校之所以與潘本不符,蓋由於惠棟與阮元不辨句讀,以不誤爲誤。此與筆誤無涉。
小結:以上四例,兩例屬於對校,本應合若符契,而結果卻出乎意外。究其原因,一則妄補,一則妄改,導致與潘本不符。一例屬於他校和本校,其與潘本不符是情理中事。一例屬於無中生有,無事生非。四例之中,有三例違規操作,令人驚詫,這未免讓讀者對“校讐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犁然備具,爲之稱快”的話打上個小小的問號。
下面讓我們看看《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禮記正義編後記》作者對“惠棟校宋本”的看法。《編後記》作者認爲“惠棟所據宋本即潘氏本”,並論證云:
潘氏舊藏本是否當年惠棟所校宋本?多年來不少學者表示懷疑,根本原因在惠校所言宋本文字與潘本不符。惠校文字與八行本不符,或當由於過錄者之失(例子另詳)。惠校文字,或爲惠校據宋本自爲筆記,並非照錄宋本文字(例子另詳)。惠校文字,亦當有惠棟據其他材料記錄異文之處(例子另詳)。惠校文字,亦當有惠棟據文義校定之處(例子另詳)。惠校文字,亦當有惠棟之備忘筆記(例子另詳)。右列諸例可知,所謂“惠棟校宋本”,內容頗雜,非皆宋本文字。近代以來學者,往往單純以爲凡《校勘記》言‘惠棟校宋本’者,除容有傳寫譌字之外,悉皆惠棟所據宋本文字,因而無法理解其與潘本之差異,不得不認爲潘本當非惠棟所見宋本。
《編後記》作者認爲“惠棟所據宋本即潘氏本”,這個結論筆者完全同意。《編後記》作者說:“多年來不少學者表示懷疑,根本原因在惠校所言宋本文字與潘本不符。”筆者则認爲,“惠校所言宋本文字與潘本不符”只是表象,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阮元“惠棟校宋本”這一錯誤表述。正是這一錯誤表述誤導了不少學者,使他們費時耗力,做了大量無用功。《編後記》作者的說法,是顛倒了因果關係。《編後記》作者又說:“近代以來學者,往往單純以爲凡《校勘記》言‘惠棟校宋本’者,除容有傳寫譌字之外,悉皆惠棟所據宋本文字,因而無法理解其與潘本之差異,不得不認爲潘本當非惠棟所見宋本。”這是把板子打到近代以來學者屁股上,有失公允。挨板子的應該是阮元,阮元是這一麻煩的製造者。試問,不僅前代學者被誤導,後代學者亦被誤導,前仆後繼;不僅中國學者被誤導,日本學者也被誤導,不分中外。面對此種反常現象,我們還不該有所反思嗎?至於《編後記》作者所據五例,則別具隻眼,多有可取,茲逐例詳說之,兼以管見附焉。
例一:“惠校文字與八行本不符,或當由於過錄者之失。如《檀弓下》‘晉獻公之喪’節,十行本分兩段,下段孔疏開頭標起止作‘稽顙至遠利也’(卷九第十葉),而《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無此六字。’今按八行本作‘稽顙至利也’(卷十二第十二葉)。不難想象,當初惠棟在毛本‘稽顙至遠利也’之‘遠’字旁批注‘宋本無’,過錄者誤會惠棟原意,以爲宋本皆無此起止六字。”
呂按:筆者基本上同意《編後記》作者的結論,需要修正的是,惠棟自言“今以北宋本校毛本”,並非以北宋本校十行本,所以不需要把十行本扯進來。毛本卷九的十三葉A面六行正作“稽顙至遠利也”,惠棟正是在毛本“稽顙至遠利也”之“遠”字旁批注“宋本無”,過錄者誤會惠棟原意,以爲宋本皆無此起止六字。就惠棟而言,這是惠棟忠實于對校的一個典型例子。
例二:“惠校文字,或爲惠校據宋本自爲筆記,並非照錄宋本文字。如常盤井在三七年《校記》卷首中指出,各卷尾題‘禮記正義卷第幾終’之‘終’字當爲惠棟所加。”
呂按:此例不唯常盤井言之,潘宗周《校勘記》言之更早,上文已有論述。此例是惠棟使用對校法之例。陳垣論對校法云:“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法。其長處在不參己見。”惠棟違背對校法原則,參以己見,畫蛇添足,導致二本之不相合也。
例三:“惠校文字,亦當有惠棟據其他材料記錄異文之處。如《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注‘終於南呂’,諸本皆如此,八行本(卷三十一第一葉,足利本原版,潘本補版)、十行本(卷二十二第六葉)亦然,而《校勘記》引‘惠棟校宋本“呂”作“事”’。按此注,《釋文》作‘南事’,孔疏云:‘諸本及定本多作“終於南事”。’是惠棟據《釋文》、孔疏記異文,非錄宋本異文。”
呂按:此例,潘宗周《校勘記》亦有論說:“呂,阮校惠校宋作‘事’。按‘事’字與《釋文》合,與《正義》不合,不得定其孰是。”《編後記》作者云:“是惠棟據《釋文》、孔疏記異文,非錄宋本異文。”誠然。然則是惠棟使用他校法也。實際上,孔疏此處已將作“呂”作“事”的來龍去脈交代得一清二楚,惠棟講不出什麼新的東西,徒記異文,有濫竽充數之嫌。
例四:“惠校文字,亦當有惠棟據文義校定之處。如《月令》孟冬‘大飲烝’注‘燕謂有牲體爲俎也’,八行本(卷二十五第十二葉)、十行本(卷十七第十三葉,阮刻經挖改)皆如此,而《校勘記》引‘惠棟校宋本作“烝”’。此處‘燕’乃顯譌字,孔疏亦可證,惠棟自當校改,無須版本依據。”
呂按:《編後記》作者所論是也。今有所芹獻者,第一,此惠校據毛本,毛本作“燕”,見毛本卷十七之十八葉A面8行,不必牽扯十行本也。第二,此惠棟使用本校法也。陳垣論本校法云:“本校法者,以本書前後互證而抉摘其異同,則知其中之謬誤。至於字句之間,則循覽上下文義,近而數葉,遠而數卷,屬辭比事,牴牾自見,不必盡據異本也。”毛本卷十七之十八葉B面8行孔疏徵引此條鄭注即作“烝”,不作“燕”,惠棟據之而出校也。
例五:“惠校文字,亦當有惠棟之備忘筆記。如《禮運》‘是謂合莫’注‘《孝經說》曰上通無莫’,諸本皆如此,而孔疏云‘正本“元”字作“無”’,八行本(卷三十第十三葉)、十行本(卷二十一第十八葉)皆同。《校勘記》引‘惠棟校宋本“無”作“无”’。惠棟據孔疏,推論此處‘元’譌‘無’,乃由‘元’‘无’形近,‘无’‘無’相通而生,遂記一‘无’字,實於宋本無關。”
呂按:《編後記》作者云:“惠棟據孔疏,推論此處‘元’譌‘無’,乃由‘元’‘无’形近,‘无’‘無’相通而生,遂記一‘无’字,實於宋本無關。”實是通達之論。唯爲了從理論上解決問題,與其訴諸某種具體現象,不如訴諸校勘方法。校勘方法有四,此例惠棟使用理校法也。陳垣先生云:“段玉裁曰:‘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所謂理校法也。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法須通識爲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爲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或曰:陳垣,近人也,以其校勘四法繩諸惠棟,可乎?答曰:陳垣雖爲近人,而其所論校勘四法乃是對西漢劉向以來校勘方法之總結。故其論對校法則引劉向,論他校法則引北宋吳縝,論理校法則引清人錢大昕也,烏乎不可!
潘宗周、常盤井賢十、《編後記》作者,此三大家對“惠棟校宋本”的論述,筆者平議已畢。至此,竊以爲,我們可以對阮元“惠棟校宋本”這個表述做出如下總結:
第一,“惠棟校宋本”是個錯誤的表述。二百年來,《禮記》學界之所以對于“惠棟校宋本”的與潘本合與不合,一直糾纏不休。究其原因,乃阮元表述錯誤所致。假設當初表述作“惠棟校毛本”,不知將省卻多少無謂的麻煩!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豈虛言哉!
第二,在我們被錯誤表述牽著鼻子走,不得不去分析“惠棟校宋本”的與潘本合與不合時,切忌從微觀上逐例孤立地去認識,而應從宏觀上建立提綱挈領之法。這個提綱挈領之法,即陳垣總結的校勘四法。如果我們這樣做了,千變萬化的複雜現象就變得條理秩如。凡惠棟採用對校法者,皆與潘本合;凡惠棟採用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者,皆與潘本不合。這是通例。惠棟採用對校法而與潘本不合者,很少見,乃事出有因,這是特例。認識到上述通例與特例,可知所謂“惠棟校宋本”與潘本的合與不合皆是合情合理之事,毋庸詫異。而“惠棟校宋本”之宋本即潘本,亦毋庸置疑。
第三,惠跋云:“校讐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犁然備具,爲之稱快。”透露出惠棟對自己的校勘成果的自信與自豪。對此,我們要一分爲二。首先,肯定惠棟的校勘成績是巨大的;其次,惠校並非十全十美,其失校、誤校、無中生有之校,亦不少見。對此,本文上文已經有所觸及,而潘宗周《校勘記》卷四十五一卷之中即指出惠棟漏校有九處。安得他日對惠校逐條審核,從統計學上對惠校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以徹底了結此段公案。
最後,正事說畢,拐回頭來再說說上文暫且擱置的問題。筆者對惠跋中“四百年來闕誤之書”一句大惑不解,籲請學界同仁有以教我。關鍵是“四百年來”四字,苦思不得其解。涉事的兩部書,一部是南宋本《禮記正義》,一部是毛本《禮記注疏》。南宋本《禮記正義》的問世時間已知是宋光宗紹熙壬子(1192),毛本《禮記注疏》的問世時間,據毛本書後的篆文牌記“皇明崇禎十二年歲在屠維單閼古虞毛氏繡鐫”,亦可確知。崇禎十二年,即公元1639年。按:乾隆十四年(1749),惠棟據宋本校毛本,由此上推四百年,則是1349年。而1349年,是元武宗至正九年。由此可知,從惠棟校書的1749年往上推四百年,與宋槧《禮記正義》不沾邊。而從毛本問世的崇禎十二年(1639)到惠棟校書的乾隆十四年(1749),中間不過一百一十年,與“四百年來”之數亦不相符。無論怎樣算,都與“四百年來”對不上號。問題在哪裡?亟盼知者有以教我。
作者單位:
呂友仁,河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呂 梁,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本文原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九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此次推送略去注釋,引用請依據原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