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回想在他的主持下一起编《儒藏》的日子,难忘情景历历在目;汤先生学者风范流韵无穷,永远激励着我们。
记得是在2003年夏秋之交,先后接到汤先生和吴志攀校长的电话,希望我能参加 《儒藏》编纂工作。当时自己颇有些犹豫,一是编纂《全宋诗》时的难处和压力记忆犹新,二是《儒藏》工程浩大,令人敬畏,同时也还存在其他疑虑。但是《儒藏》编纂毕竟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承蒙领导期望,只能勉为其难受命。当然为了能踏实投入工作,我也没有轻易放过自己的疑虑,而是不断通过加深认识,科学实践,加以排解。例如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报》2003年11月13日第五版上的拙文《对编纂〈儒藏〉的几点看法》,其中“去惑除疑”一节的内容,不是泛泛谈释疑解惑,也有针对自己讲的成分。
在汤先生麾下合作编《儒藏》的十一年中,汤先生作为项目首席专家,不顾年高病患,尽心操劳,率先垂范,使自己深受教益,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汤先生勇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汤先生深谙《儒藏》工程担子的沉重,加之自己年事已高,难上加难,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担当起来。他不止一次表示自己的坚决态度,如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接受这个任务时是76岁,这么大的岁数接受这个任务是冒险”,“这个工程要十六七年才能完成,我能不能活到那时候都是问题。而且这项工作非常损耗人的体力和精神,我每天要很操心,事无巨细都要考虑。我是搞研究的,没有管理经验,现在也要一点点学;我是个学者,我要写书,但现在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7月10日第 12版 )。汤先生这样做,固然与他一贯秉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祖训的为人处世原则有关,具体到承担《儒藏》工程而言,更有其对此事高瞻远瞩的动力。汤先生认为“历史上儒、道、释三家并称,但三家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儒藏》“将使我们有一部最完备最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这不仅使我们可以更系统、更全面地了解儒家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也是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使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得以利用中国文化资料验证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今天,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前夜,重新回顾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源头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必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重大作用。为了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把儒家经典及其各时代的注疏和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以及体现儒家思想的各种文献,编纂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儒藏》,无疑对当前和后世都十分必要,特别是对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明新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上海 《社会科学报》2003年11月13日头版《北大启动〈儒藏〉编纂工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谈编纂 〈儒藏〉 要旨》)。
后来在2013年年底和2014年年中,笔者先后参加汤先生大著《瞩望新轴心时代》、《汤一介集》出版座谈会,全面学习了汤先生著述,深入地了解了汤先生的学术、文化思想,对他勇于承担《儒藏》工程思想渊源和强大动力又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正如自己在《瞩望新轴心时代》大著出版座谈会的发言所说:“汤先生有高瞻远瞩的大视野,他所谓的瞩望,就是能站在制高点审视我们整个时代,但又不是好高骛远,而是脚踏实地。汤先生是立足于中华文明、立足于我们祖国来考虑问题的,他更关心的、考虑更多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新文化,是当下民族的复兴、文化的繁荣。但是,汤先生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不是自我封闭,不是妄自尊大,他是从整个世界文明的角度、从世界各种文明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角度来考虑的,并在世界文明当中考虑中华文明的地位,以及在21世纪,中华文明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贡献。我们知道,长期以来,由于西方的强势和偏见,西方文化占据了中心地位,中国的文化被压制、被扭曲、被边缘化了。世界不了解我们,甚至我们自己也不了解自己:没有自信,没有自立,没有自觉。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文化自觉的问题。如今,汤先生又提出反本开新的命题,我们既不能自我封闭,又须与时俱进,这些都是非常可贵的。他强调所谓新轴心时代,就是多元文化的时代,多元文化共存,共融,和而不同,对话交流,融会贯通,互利共赢······汤先生勇于担当,以《儒藏》编纂为例,汤先生在这项工程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的原则,充分体现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风格。为此甚至达到忘我的境界,忘记了年龄,忘记了健康,使我们深受感动。因为文化绝不是空架子,而是有依托、有载体的。现在,有些搞文化研究的人往往流入空谈、奇谈,不务实际。离开文本,离开载体,还有什么文化可谈。汤先生坚持编好《儒藏》,就是要为儒学研究和弘扬提供可靠的文献、文本。”
《儒藏》“精华编”采取什么形式编纂出版,开始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影印出版,另一种是校点排印出版。前者相对容易得多,但会与已经出版的一系列大型影印丛书形成重复、造成浪费,而且不便于利用;后者立足现代,方便当今海内外读者的阅读,以及得以与数字化接轨而便于检索、利用。当然后者提高了编纂工作的学术标准,增加了编纂工作的学术含量,也相应极大地增加了整理、出版的难度。尽管如此,编纂中心在汤先生的主持下,还是决定迎难而上,采取后者的做法。而且汤先生对此早已有高难的设想和追求,如他在接受《信报》记者采访时曾说:“之所以提出要编纂《儒藏》,是因为受了《佛藏》的刺激。我们现在通常用的《佛藏》是日本人的排印本《大正藏》,《佛藏》有很多影印本,影印本当然有其价值,但用起来麻烦,不方便,所以现在全世界研究佛教的人引用的书仍是日本大正年间编纂的《佛藏》。我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让世界的研究者都用我们的东西。”(《信报》2005年7月10日第12版) 可见汤先生不仅有敢于担当的精神,而且有如此宽阔的胸襟,实在令人感佩。
第二,使笔者深受教育的是汤先生的民主学风和科学决策。汤先生是一位有声望的大学者,但是他非常谦和,平等待人,遇事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集思广益,然后做出科学决策。
汤先生称,《儒藏》的编纂出版有三大难题,即经费筹措难、人才招徕难、组织协调难(《新京报》2005年9月24日《儒藏》样书出版采访记)。其中后两大难,主要是靠民主学风和科学决策来化解的。
从大的范围来看,《儒藏》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以北京大学为依托,联合海内外近百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近500位专家学者一道参与工作,广揽人才、组织协调之难,不言而喻。汤先生为此费心尽力,时时刻刻从大局考虑,一方面根据编纂工作的进程,针对主要问题,组织大规模的专题研讨会议,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不避分歧,提倡争论,以化解分歧,取得共识;一方面亲自或派人到各协作点了解情况,讨论并解决问题。又如《儒藏》增收“域外汉文儒学文献”以反映东亚儒学文化圈的情况,是2006年应韩、日、越三国学者的建议而晚一步决定的,汤先生非常重视这一工作,亲自到日本、韩国分别与户川芳郎教授、梁承武教授等学者筹划落实有关工作,并派人到越南与阮金山、丁清孝教授等学者筹划落实有关工作,后来还多次请他们来中国参加编纂研讨会议。因为《儒藏》整理是国内大范围的协作,甚至涉及海内外的协作,为避开“成于众手、多遭诟病”的编书陷阱,搞好队伍团结、保证书稿质量至关重要,而这一点也只有靠发扬民主学风、坚持科学决策,才能做到。举一个有关处理书稿的例子:在编纂样书时遇到一部出土《论语》竹简书稿,此书已经出版,而且颇具影响。本来原封不动收入《儒藏》样稿以作范例,后来发现原书在校勘上有不少问题,不仅不符合《儒藏》体例,而且异文的判断抉择存在硬伤,古文字释文亦有误处,如收入《儒藏》,非经过较大修改不可。我们把修改的书稿样本寄给原整理者审阅,希望以此为准,作为编入《儒藏》的新稿。可是他们又完全作了回改,恢复了错误的原貌。我们又写了一封近五千字的长信,具体指出原书的错误,说明修改的原因和依据,跟原整理者再行商讨。汤先生对此很重视,拿到信后,分别请庞朴先生、李学勤先生过目,然后亲自把信寄给原整理者,希望他们参考修改,而原整理者认为原书是经过与一些老专家一起定稿的,坚持不作改动。事已至此,总不能知错不改,以讹传讹,于是不得不决定只采用原书的释文,改由《儒藏》中心另作校勘。
除了与编纂整理单位和人员的外协关系之外,还有与审稿专家及出版社的外协关系,也都要靠发扬民主学风、坚持科学决策来协调。从《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内部小范围来看,在汤先生的主持下,也是民主和谐,科学从事。通过汤先生的组织协调,《儒藏》中心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集中统一,很快建立了一整套规章制度, 拟定了一系列条例细则,策划了严密可操作的编纂工作流程,使《儒藏》系统工程很快走上科学有序之路。还有两点经验尤为可贵:一是编纂工作分“精华编”、全本两步走的科学决策;一是按序编定,分册整理,不拘先后,滚动出版的实效操作。前者使《儒藏》分阶段出成果成为可能,而不至于不切实际,幻想毕其功于一役, 旷日持久,遥遥无期;后者使《儒藏》成书成熟一部推出一部,既可使成果及时面世,发挥效益,又可使整理者及早看到自己的收获,于心为安。
第三,汤先生有远见卓识,以人为本,强调出成果与出人才的辩证互惠,关心人才培养,并十分珍视和培育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的团队。
汤先生深感《儒藏》编纂“招徕人才难”,一再强调“这项工作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这个项目牵扯文史哲、图书馆、考古等专业知识,能干这个活的人并不多。现在做《儒藏》已经有些晚了,做《二十四史》的那批老先生大都已经故去,老专家没剩下多少了,再过十年八年几乎没有了,会出现人才断层。现在做《儒藏》带有抢救性质,一方面要抢救这些老专家的学识,另一方面也要抢救书,还要培养新的人才”(《信报》2005年7月10日第12版采访记)。因此他亲自带头,与《儒藏》中心的教授共同招收博士生,并引进博士后,紧密结合项目具体实践进行培养提高,这不仅增加了编纂工作的人手,而且培养出新生人才。在学校领导支持下成立的实体机构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是《儒藏》编纂的可靠基地,通过调进、留毕业生、返聘等多种途径,很快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以中青年为骨干的学术团队。这个团队与校内外协作单位部类主编和广大校点者、审稿专家密切联系,与北大出版社默契配合,形成《儒藏》编纂出版整个链条的有效周转机制。
汤先生尤其重视对《儒藏》中心中青年人员的重用和培养,既授以责任编委的重任,又引导他们及时总结工作经验,增长才干。记得在2012年3月,汤先生提出让责任编委就个人的情况普遍进行一次审稿编纂工作的总结,并建议由我加以汇总,结合古文献学理论和编纂工作的实际综合谈一谈,目的在于提高编纂工作的水平,以便保证、提高书稿的质量。这次总结,大家非常认真,涉及内容丰富,认识水准很高,经验切实可行,效果甚佳。汤先生虽然重病缠身,事先还特别关照,希望综合总结时能亲自到会听一听。汤先生还十分关怀《儒藏》中心的学术梯队建设,曾亲自签署《儒藏》中心申请下达正高职称指标的报告,至今尚未得到解决。为稳定人心,发挥积极性,巩固团队,希望校领导全面落实有关《儒藏》中心科研系列职称评定的措施。
汤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两年了,临终时他并未对我们留下特别的嘱咐。但是我们永远记得他辞世前两个月在《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上的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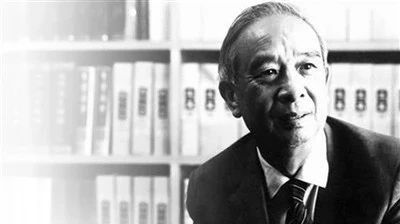
卫红部长、邬局长、北大的朱善璐书记: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次会议,同时,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团队,因为没有这个团队,十年的努力是完成不了这么大的工程的。我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的时候,就希望继续把《儒藏》的“大全本”完成。因为如果不完成“大全本”的话,就说明 《儒藏》并没有完成,只是完成了部分。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把“大全本”完成。在这个一百册出版的时间,我想我们的团队,参加这个工作的同志都有这个心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努力,能够早一点把这个伟大的工程实现。
这样一个工程,是一个跨国界的工程,我们联系了日本、韩国和越南的学者一起做。它不是一个小的跨国界的工程,而是一个大的跨国界的工程,所以,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很多同志以往都支持过我们,特别是张东刚同志支持我们,还有其他的很多同志都支持过我们,使我们非常受鼓舞。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这个工程来尽我的力。我不能多讲话,医生在这里监督我不能多讲话,老朋友杨庆存主任也在这,所以,谢谢大家,我就讲这些。部长先生,书记先生,谢谢!谢谢!
当时汤先生是坐着轮椅来参加会议的,他被几个人搀扶着上主席台入座的情景,使我们不忍回忆。这次发自肺腑的朴实讲话,留下了汤先生的最大心愿。他念念不忘《儒藏》工程,不忘其伟大意义,不忘其未竟之业,不忘感谢支持《儒藏》的领导和人士,寄厚望于他信任的团队。作为这个团队的成员,我们一定牢记汤先生的遗愿,依靠领导支持,克服种种困难,继续把《儒藏》编好。
2016年9月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儒藏》“精华编”总编纂)
本文收入《汤一介与〈儒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