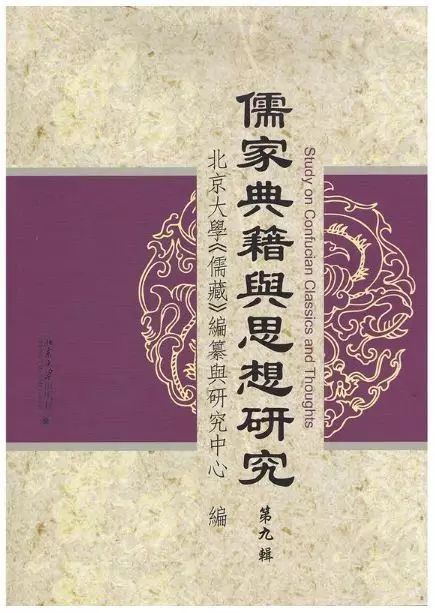(北京大學哲學系、《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內容提要】 湯師一介先生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研究儒學,特別關注儒學現代化問題。他是從“新軸心時代”儒學復興、儒學“第三期發展”、儒學的“現代化”等多角度對此問題進行探索的。湯先生嘗試從哲學的角度出發,主張對儒學進行現代的解釋,此解釋總體上可以概括為兩大部份:“三個合一”、“三大理論”。“三個合一”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大理論”即“普遍和諧”理論、“內在超越”理論、“內聖外王”理論。湯先生認為,儒學的以上理論對解決當今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
 《汤一介集》书影
《汤一介集》书影
湯先生的學術研究與其父親湯用彤先生對他的影響是分不開的。湯用彤先生的學術研究主要在佛教史、魏晉玄學,晚年又開始閱讀《道藏》,寫了一些頗有影響的道教論文。湯用彤早年對儒學有過研究,寫過為數不多的文章,如《道德為立國之本議》《理學譫言》等。湯先生雖然在“文革”之前即寫過儒家傳統當中有關孔子、孟子、董仲舒等的論文,但主要是承續湯用彤先生而做的進一步的研究,所以早期對儒學關注不是很多。因此,真正開始研究儒學是比較晚的,1983年是關鍵的一年。據湯先生自述:
1983年,我在美國碰到了新儒家的問題。以前我對儒學沒有興趣,可以說不研究儒學,我是研究魏晉玄學的,還研究一點佛教、道教。我從1983年開始考慮新儒家問題,新儒家的基本觀念。
對於湯先生哲學思想的發展來說,1983年參加第十七屆世界哲學大會是非常重要的機緣。通过這次會議,湯先生結識了不少海外研究中國哲學的朋友,而且也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湯先生為這次會議專門做了長時間的準備,並將自己之前一直思考的哲學普遍問題,結合儒學進行了專門的發言。湯先生在晚年回憶道:
從我關注和研究的興趣上看,我原來更喜歡道家和佛教。只是在1983年我到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時感到海外學者更重視儒家學說。於是,我開始讀一些海外儒學研究學者的著作,而有所得。這時正巧要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辦第十七屆世界哲學大會,會議邀請了我。為了參加會議,我花了兩三個月寫了一篇《關於儒家思想第三期發展可能性的探討》的論文,並在大會中的“中國哲學圓桌會議”上作了發言。
湯先生的弟子胡仲平老師曾對筆者講,湯先生在第十七屆世界哲學大會上的發言代表了湯先生學術研究上的一次“頓悟”,猶如王陽明的“龍場悟道”一般。筆者以為,這樣的看法可能是允當的,湯先生自己或許也隱隱感覺到這一點,這體現在上引中的“有所得”三字。《關於儒家思想第三期發展可能性的探討》一文,湯先生後來修改成為《論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真、善、美問題》一文發表。湯先生在此文中將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下簡稱“三個合一”)分別對應於“真善美”三大普遍價值。
湯先生晚年所承擔的主要任務是《儒藏》工程,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湯先生仍惦記着儒藏》工程的未來規劃。2014年11月15日,樂黛雲先生整理出“關於湯一介遺願的報告”(未发表),主要內容即是《儒藏》(全本)的落實以及《儒藏》(精華本)出齊之後對之的推廣學習。湯一介先生生前最後一次講話是“第七屆三智論壇”的視頻寄語,錄製於2014年8月23日。其中講到“三個合一”與“真善美”等問題。據湯先生臨終前日夜陪護在其身邊的劉美珍女士講,湯先生在病床上曾喃喃自語“真善美”三個字。由上不難看出,湯先從1983年以來,始終都在關注着儒學的問題。
湯先生對儒學的研究主要是從宏觀的文化角度來把握,關注的重點在於儒學的現代化的問題。應該說這一問題是現代以來,被稱之為“現代新儒家”、“當代新儒家”,以及其他很多儒學學者、儒學研究者、儒學弘揚者等所關注的問題。由於筆者學力不逮,無法與眾多海內外有關儒學的研究进行對比,下面僅就湯先生的儒學研究做一梳理,就教於方家。
關注核心:儒學的現代化
湯先生曾提出“復興儒學必須有問題意識”:
復興儒學要有“問題意識”。當前我國社會遇到了什麼問題,全世界又遇到了什麼問題,都是復興儒學必須考慮的問題。對“問題”有自覺性的思考,對“問題”有提出解決的思路,由此而形成的理論才是有真價值的理論。
湯先生所言問題意識,實際上即是儒學的現代化的問題。儒學在現代的價值就在於要解決當今社會所出現的問題。湯先生特別強調有“自覺性”的思考,這是指理論的研究要有明確的目的意識,不是盲目地建構。對於當今社會存在的問題,不同學者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湯先生則將之明確歸納為“三種矛盾”:
看看目前我們的人類社會存在着種種威脅人類生存的問題,概括起來可以說存在着三大矛盾:人和自然的矛盾;人與人(擴而大之就是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矛盾;人自我身心(內外)的矛盾。這些矛盾可以說越來越尖銳地威脅着當前人類生活的諸多方面。那麼儒家思想文化能否為消除這些矛盾,引導人類社會健康、合理的發展提供有意義的精神資源呢?
人類社會遇到什麼問題是湯先生所謂“問題意識”的一個方面,而儒家思想如何化解這些問題則是“問題意識”的另一方面。湯先生對儒學的研究在一個非常宏觀的視閾之下,其語境當中,儒學在“新軸心時代”的復興、儒學的“第三期發展”、儒學的“現代化”等都具有大致相同的義涵。
湯先生是國內“新軸心時代”說的大力倡導者。在他看來,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新的世界範圍內的“新軸心時代”的前夜。湯先生指出:
在進入第三個千年之際,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現了對“新軸心時代”的呼喚,這就要求我們更加重視對古代思想智慧的溫習與發掘。
在“新軸心時代”,世界上的各大文明都將再一次得到“復興”的機會。儒家文化自然也不例外。湯先生滿懷信心地認為,“新軸心時代”必定會到來,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是我們並不能消極等待。我們要積極地發揚自己的傳統,當然包括儒學,以期為人類社會做出重大貢獻。
儒學的“第三期發展”問題,是湯先生、杜維明先生等都特別關注的問題。用湯先生的話說:
如果我們說先秦儒學是儒學的第一期發展;宋明儒學(包括理學與心學等)是儒學的第二期發展,它是在受到佛道兩家的衝擊後形成的新儒學,並曾傳播到周邊國家,發生了重大影響;那麼,現代新儒家則是16世紀以來,在西方文化衝擊下的儒學的第三期發展。
由此可見,在湯先生看來的儒學“第三期發展”實質上是儒學如何應對西方文明的衝擊問題。湯先生本人在父親湯用彤先生的研究基礎上,對佛教傳入中國形成的中國化佛教有深刻的體會。湯先生認為,中國文化經歷了幾百年的時間,不僅成功地吸收和改造了印度佛教形成中國化的佛教,而且儒家能夠吸收佛教思想創立宋明理學,影響後來的中國社會近千年。儒學的“第二期發展”成功地應對了來自印度佛教的挑戰。從16世紀即開始的“第三期儒學”是否能夠成功地得到發展,現在還沒有確定結論。湯先生認為:
但是,這第三期儒學的發展是否能取得應有的突破呢?我認為還要觀察一個時期,才能作出結論。因為,就目前情況看,現代新儒學思潮無論在臺灣、大陸或其他地區都還沒有形成氣候,正如杜維明教授所說:“儒門淡薄”。
當前學術界流行所謂“現代新儒家”第一代至第四代的說法,還有所謂“港臺新儒家”、“大陸新儒家”等說法。湯先生在1994年的看法是“沒有形成氣候”。可見,儒學思想的探討與研究,以及儒學思想的創造性建構,在湯先生當時看來,還是很不夠的。
儒學的“現代化”也是同樣的問題,不過是採取不同的角度。從中國的立場來看,現代化的問題主要是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造成的。現代化有很多方面。比如,語言文字上使用白話文,使用簡體字等都是現代化的產物。此外,日常生活等方面還有無窮無盡的現代化的產物。現代與古代在諸多方面已然存在着一種深深的鴻溝。在思想文化方面,為了更好的現代化,我們曾經人為地中斷傳統。但是後來人們逐漸認識到,斬斷了文化的根,就會成為生活在本土上的異鄉人。湯先生在一次講演中提到:
我們需要回顧自身文化的發展,找回自身文化的根子,並且在自身文化的基礎上來迎接一個新的時代。一個民族自身的文化根子培育得越好,它吸收外來文化的能力也就越強。
在湯先生看來,中國文化的根是其儒釋道文化,而儒學在中國歷史上曾居於主流地位。把這個根子培育好,就存在儒學的現代化問題。根據湯先生的歸納,目前學界以及社會上存在大約四種儒學“現代化”的主張:
(l)儒學現代化就是要使儒學成為中國現代社會的主導思想;(2)儒學現代化就是使它按照西方文化的模式改造;(3)儒學現代化就是把儒學馬克思主義化;(4)儒學現代化即是要用它來解決現代社會的一切問題。
這四種主張,湯先生沒有展開敍述,也沒有具體列出其代表人物,但是湯先生對這四種主張全部都不同意。湯先生認為,如果從以上四個方面來理解儒學“現代化”的問題,一方面,儒學不可能現代化,另一方面,即是現代化了,也沒有什麼好處。湯先生認為:
但是對“儒學現代化”能否做另外的理解,即“儒學現代化”是說對“儒學”做現代的解釋。我認為,這樣或許是可以的,而且如果可以對儒學做出現代的解釋,那麼儒學就仍有其現代意義。
對儒學進行現代解釋,這是湯先生認為發展與研究儒學的關鍵。因此,從總體上說,湯先生對儒學研究的關注核心在於儒學的現代化,而儒學要能夠在“新軸心時代”復興,要有“第三期發展”,要能夠真正“現代化”,對儒學進行現代的解釋是其中的關鍵。
筆者認為,湯先生正是在研究儒學現代化的視野之下,從哲學的角度出發,主張對儒學進行現代的解釋。湯先生對儒學的現代解釋可以概括為:“三個合一”、“三套理論”。
三個合一
2009年,湯先生將自己所寫的有關儒學方面的論文編為一部論文集,題為《儒學十論及外五篇》,後來在編文集時,又在其基礎上增補了十幾篇文章,作為《湯一介集》第五卷,卷名為“在儒學中尋找智慧”。湯先生對儒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此一卷當中。該卷收入湯先生在1983年第十七屆世界哲學大會的發言底稿《關於儒家思想第三期發展可能性的探討》,其中提出“貫穿整個儒家思想發展過程中有兩個基本精神對我們今天仍有很大意義,一是理想主義,二是人本主義,而這兩者優勢結合在一起的。”其中在說明人本主義的時候,特別講了“三個合一”是中國傳統哲學關於真善美的三個基本命題。雖然指說是中國傳統哲學,但所舉的例子卻都是儒家的。此處兩種基本精神,在後來以《關於儒家思想第三期發展可能性的探討》為基礎寫成的《論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真、善、美問題》一文中擴展為四個基本方面:
儒家哲學凝聚而成並長期影響着我們這個民族的或許有以下四個方面,即空想的理想主義、實踐的道德觀念、統一的思維方式、直觀的理性主義。
一、空想的理想主義。儒家嚮往某種理想的社會,並期望在現實社會中實現這樣的理想。湯先生指出:
照儒家看,理想社會就是一種理想,它只有實現的可能性,但並不一定能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性。儘管理想社會從來沒有實現過,但要不要追求它卻是一個根本性問題,是一個人生態度問題。
因為這樣的理想從沒有實現過,所以具有“很大的空想成分”。
二、實踐的道德觀念。湯先生認為,儒家哲學有人本主義的傾向,但與西方近代的人本主義不同。他指出:
西方的人本主義把“人”作為單個的個人,強調個性解放,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而中國過去社會裏的“人本主義”可以說是一種“道德的人本主義”。
儒家不僅將“人”放在一定關係當中考察,而且從“人”出發來探討“人”與“天”之間的關係,強調“天人合一”,即天與人的統一性。
三、統一的思維方式。湯先生認為:
中國傳統哲學的理論思維方式,從一開始就注重一對概念的統一關係或諸種概念的相互關係。《易經》系統以乾、坤(後來以陰、陽)為一對對立統一的概念,而《洪範》則以五行之間的對立統一關係立論。
這主要指儒家思想具有的和諧與統一的觀念。
四、直觀的理性主義。湯先生指出:
儒家哲學強調“心”(理性)的作用,自有其可取之處。強調“心”的作用,即強調人的主動性,強調人在宇宙中的核心地位,而人之所以能是宇宙的核心,正在於人有“明德”之心。人的理性又是帶有道德性的,宋儒認為“仁”是心之體,可見儒家哲學有道德理性主義的傾向。但是,對於為什麼“心”有如此之作用、如此之特性的問題,則很少分析;對“心”的作用的過程(心理活動之過程)更缺乏具體分析,致使儒家哲學成為一種直觀的道德理性主義。
如果說對於上述“四種精神”,湯先生是辯證地看待,肯定其作用的同時還指出其局限性的話,那麼“三個合一”則完全是從正面來進行肯定,認為是儒學當中可以為現代社會所繼承發揚的內容,後來還專門對其中每一個合一進行專門的論述。
湯先生“三個合一”的思考與他對人類社會普遍價值的探索有密切關係。在湯先生看來,真善美三者具有某種恒久的價值。在世界範圍內的中國、西方、印度三大文明都在追求真善美。組成中國文化的儒釋道也都在追求真善美。西方對真善美追求的起源可以用亞里士多德的三部著作作為代表,即《形而上學》《尼各馬可倫理學》《詩學》,分別代表哲學、倫理學、美學。印度以佛教思想為頂峰,佛教主要講佛法僧三者。對於中國哲學,特別是其中的儒家哲學,湯先生用“三個合一”來對應,這一點確實是出於湯先生的別出心裁。
一、“天人合一”。湯先生在“三個合一”當中都是用“合一”來說明的,這一點是隨順人們一般的語言習慣。實際上,“合一”在湯先生的語境當中是統一性的意思。在筆者看來,“天人合一”與婆羅門教(印度教)的“梵我合一”是不同的。在婆羅門教看來,作為宇宙實體的“梵”與個體生命“我”是同一的。兩者之間的差別是虛幻的。處在生死輪回當中的“我”,可以通過瑜伽等修行,最終達到與“梵”的同一,獲得解脫。中國思想家往往將“天人之際”看作是最為根本究竟的哲學問題。雖然歷史上也有思想家強調天人的相分,但是在湯先生看來,儒家的主流“大都把論證‘天人合一’或以說明‘天人合一’為第一要務”。湯先生發現,在出土文獻郭店楚簡《語叢一》中有“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的話,是最早“天人合一”的明確表達。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將天“與人相副”,是“天人合一”的學說,而宋儒的身心性命之學更是建立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礎之上。限於篇幅,這裏不詳細轉述湯先生對“天人合一”的舉例與分析。湯先生指出,“天人合一”在當今被人們重視是因為生態危機的問題。西方主流的“天人二分”思想造成了人對大自然的過度破壞,進而危機到人自身的生存。湯先生分析指出“天人合一”作為思維方式的重要意義:
它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對解決“天人關係”無疑是有其正面的積極意義,而更為重要的是它賦予了“人”以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人”必須在追求“同於天”的過程中,實現“人”的自身超越,達到理想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關於湯先生對“天人合一”的分析,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湯先生早期還從中歸納出四種獨特的思維方式:
第一,所謂“天人合一”的觀念表現了從總體上觀察事物的思想,不多做分析,而是直接的描述,我們可以稱它為一種直觀的“總體觀念”;第二,論證“天人合一”的基本觀點是“體用如一”,即“天道”與“人道”的統一是“即體即用”,此可謂為和諧“統一觀念”;第三,中國傳統哲學,不僅沒有把“天道”看成僵化的東西,而且認為“天道”也是生動活潑的、生生不息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類社會之所以應發展、人們的道德之所以應提高,是因為“人道”應適應“天道”的發展,此可謂為同步的“發展觀念”;第四,“天”雖是客體,“人道”要符合“天道”,但“人”是天地之心(核心之心),它要為天地立心,天地如無“人”則無生意、無理性、無道德,此可謂之為道德的“人本觀念”。這就是中國儒家哲學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全部內涵。
湯先生所分析的直觀的“總體觀念”、和諧的“統一觀念”、同步的“發展觀念”、道德的“人本觀念”四個方面,雖然沒有特別詳細的展開,但卻是饒有意味的,體現了湯先生作為哲學家的獨立思考精神,值得我們繼續思考。
二、“知行合一”。湯先生不從理論與實踐的認識論角度來分析知行關係,而認為知行在儒家哲學當中主要是一個倫理道德的問題。因為在儒家哲學當中,認識問題與倫理道德問題是同一問題。湯先生特別注意到,“知行合一”的講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王陽明,湯先生为此進行了分析:
如果從認識論的角度,或者可以說王陽明某些話有“合行於知”的嫌疑,但從道德修養層面上看,強調“知行合一”是有一定的合理因素的。
由此可見,湯先生所說的“知行合一”是從儒家思想角度出發的,強調的是追求善的道德認識與實踐的統一性。
三、“情景合一”。“情景合一”是湯先生對王夫之所言的“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的概括。湯先生高度評價王國維的思想,認為王國維把美學的“情景合一”論與“境界”論聯繫在一起,將美學理論提升到“天人合一”的哲學高度。
“三個合一”自身具有某種統一性。湯先生在“論‘情景合一’”一文末尾指出:
中國哲學關於“真”、“善”、“美”之所以可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來表述,這正體現著中國傳統哲學以追求一種理想的人生境界為目標,而“天人合一”正是中國的一種在“人”與天地萬物之間有著相即不離的內在關係的世界觀和思維方式。
在湯先生看來,“三個合一”中的“知行合一”、“情景合一”都是從“天人合一”中派生出來的。
三大理論
湯先生更從“天人合一”中推演出具體的理論體系來對儒家思想進行建構與歸納,即宇宙人生論、境界修養論、政治教化論三個方面。湯先生在追憶自己一生哲學探索的“我的哲學之路”一文當中,將此“三大理論”稱之為“關於中國傳統哲學的理論體系問題”的探索。
在“論‘內聖外王’”一文的末尾,湯先生說:
中國哲學理論體系中的“普遍和諧觀念”,可以說是中國傳統哲學的宇宙人生論,“內在超越問題”可以說是它的境界修養論,“內聖外王之道”可以說是它的政治教化論。中國傳統哲學的這套理論,無疑曾對人類文化做出過重要貢獻,它作為一不間斷延續了幾千年的文化傳統也必將對今後人類的文化做出其應有的貢獻。
湯先生在“我的哲學之路”一文當中對這三大理論有一個非常精彩的梳理與總結,湯先生分析了自己思想的形成過程,並簡述其主要內容,還列舉其主要代表性的論文。為避免重複,本文在此不予詳述,僅就“我的哲學之路”一文寫作之後湯先生形成的一些新思想或者筆者認為的某些重要方面,略分析如下。
一、宇宙人生論——普遍和諧觀念。普遍和諧的觀念取自儒家思想中的“太和”觀念,湯先生認為其中包含四個方面的和諧: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自我身心(內外)的和諧四個方面。這四個方面的和諧除第一個方面外,其他都關係到人。所以湯先生重點使用後三種和諧來解決人類所面臨的“三大矛盾”:人和自然的矛盾、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人自我身心(內外)的矛盾。“天人合一”的思想解決人和自然的矛盾;“人我合一”的思想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特別是更大範圍的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矛盾;儒家的“身心合一”的思想解決人自我身心(內外)的矛盾。湯先生對之有一個總的歸納:
儒家的“合天人”(合者,不相離也,即人與自然的和諧)、“同人我”(把“人”都當成是自己的同胞、兄弟,即人與社會的和諧)、“一內外”(使自我身心內外統一和諧,即人自身的和諧),是我們人類社會所應追求的。
二、境界修養論——內在超越問題。受到余英時的“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一文的啟發,湯先生對中國傳統哲學的內在超越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寫作了四篇相關論文。 “論‘內在超越’”一文是從儒家思想來討論內在超越問題的。湯先生敏銳地看到《論語》中子貢所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的話當中,包含有內在性與超越性的兩個問題。“天道”是超越性的問題,“性”是內在性的問題。此處的內在性是人的本性,是人的內在精神,如“仁”、“神明”等。此處的超越性是宇宙本體,如“天理”、“太極”等。儒家從“天人合一”出發,論證了內在性與超越性的統一性,即內在的超越性,或者超越的內在性。湯先生在此文之最後,指出儒學“第三期發展”要解決兩個問題:
即能否由此以“內在超越”為特徵的“內聖之學”開出適應現代民主社會要求的“外王之道”來;能否由此以“內在超越”為基礎的“心性之學”開出科學的認識論體系來,照我看也許困難很大。
湯先生不認為儒家的內聖之學、心性之學本身能夠推演出現代民主政治以及科學認識論體系,認為儒家思想有其優勢,但也應當吸收西方的某些長處:
如果以“內在超越”為特徵的中國傳統哲學能充分吸收並融合以外在超越為特徵的宗教和哲學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政治法律制度,使中國傳統哲學能在一更高的基礎上自我完善,也許它才可以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要求。我認為,這個問題也許應是可以認真討論的一個問題。
中西哲學思想本身各成體系,如何進行互補,確實是一大難題。目前東西方思想家都從其自身的角度對此一問題進行探索。
三、政治教化論——內聖外王之道。梁啟超曾言:“‘內聖外王之道’一語,包舉中國學術之全體。” “內聖外王”雖出《莊子·天下篇》,但後來更多為儒家所闡發。朱熹將《大學》建構為“內聖外王”的代表經典,從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而成聖,進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外王。湯先生質疑古代“內聖外王”理想的現實性,認為:
道德教化與政治法律雖有某種聯繫,但它們畢竟是維繫社會的兩套,不能用一套代替另外一套。因此,“王聖”(以有王位而自居為聖人,或別人推尊之為聖人)是不可取的,“聖王”也是做不到的,“內聖外王之道”作為一種政治哲學理論也就不是什麼完滿的理論。
但湯先生也不是完全否定“內聖外王”的積極意義。湯先生的此種看法基於一種文化立場:
如果要使它對人類文化繼續起積極的作用,我認為,一方面我們應適應現代化的要求,來使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今的全球意識下得到發展;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種哲學體系存在的缺陷,並充分吸收其他國家、民族文化的長處,使中國文化更加完善。
湯先生受羅素的一個思想的啟發很大:
不同文明的接觸以往常常成為人類進步的里程碑。
總的來說,不難看出,湯先生對儒學現代化的思考是立足於全球化的廣闊視野之下的。他身上有儒家的情懷,對儒家思想不迷信,但又對儒學思想抱有希望。湯先生從自己的體會出發,探索了儒學的現代意義等重大問題,提出了不少值得進一步思考的議題。湯先生本人特別強調理論探索的自覺性,他不是消極地等待未來,而是堅持未來可由我們自覺創造的理念。湯先生的探索在未來會有多大的影響與價值,只能交由時間來檢驗,由我們的後人來評價了。
(本文原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九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此次推送略去注釋,引用請依據原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