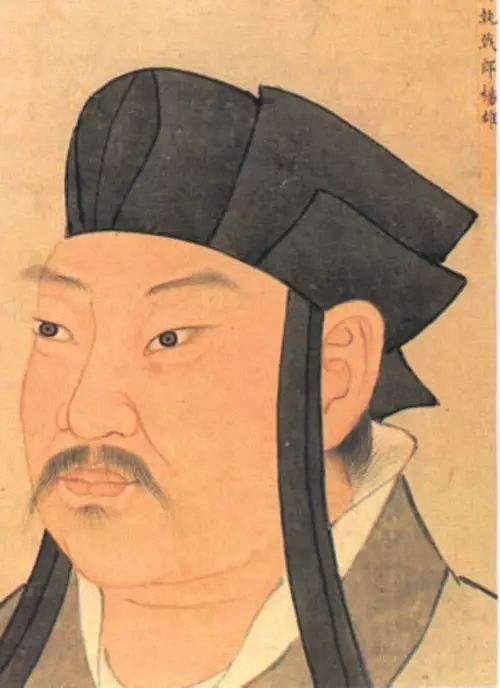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內容提要】揚雄《法言》首倡“子長愛奇”之說,其初只謂《史記》所載人物史實不皆合乎儒家道義,不可以垂範後世。後人多誤解揚雄,將“愛奇”之“奇”等同於“怪異”,認爲司馬遷耽愛奇聞佚事、怪力亂神,置史料的真實性不顧。於是,論證《史記》所載失實者,多執“愛奇”為口實;論證《史記》文直事核者,多責“愛奇”爲虛言,實皆未嘗深考。今考之文獻,爲之正名,並附帶論及愛義、愛奇之辨在學術史上之意義。
揚雄《法言·君子》云:“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錄不隱,故可采擇。淮南,鮮取焉爾。浮辯虛妄,不可承信。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或出經,或入經。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叙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此條可與《法言·問神》中論淮南、太史公者參看,其文曰:“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歎不純也。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
借助於李軌注,我們可以瞭解,這兩段文字的大意是說:《淮南子》與《史記》作爲西漢時期兩部影響巨大的著作,均內容豐富而又駁雜不純。一般人爲這種駁雜所迷惑,難於去取,而聖人以義衡量之,明於取捨,故不病於多知,不爲所惑。雖然聖人不病於多知,但二書相較,《淮南子》之用不如《史記》之用,因《淮南子》過於浮誕虛妄,可取者很少;而《史記》則秉筆直書,史實可信,可取者較多:取捨的標準,應折衷於儒家的義。司馬遷喜愛歷史,凡其人有可采,則筆之於書,加以褒揚,不以其短而棄置之;孔子喜愛歷史,則是喜愛其中合乎道義的內容。
揚雄所謂“愛義”與“愛奇”,主要是從史料是否具有垂範後世的教化意義上着眼的,以“奇”爲不正;而幷非從史料是否具有真實性上着眼,以“奇”爲怪異。除上文之解讀外,還有兩點可以證明此論。一者,揚雄上文已肯定《史記》可取者多,《漢書·司馬遷傳》贊也說“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則揚雄極贊《史記》爲實錄,自然不會責其怪異不可信。二者,後人注解《法言》者亦不以“奇”為不可信。“多愛不忍”宋咸注說:“遷之學不專純於聖人之道,至於滑稽、日者、貨殖、遊俠,九流之技,皆多愛而取,不忍棄之。”吳祕注曰:“不可以垂世立教者,司馬遷皆敘而録之,是多愛不忍也。”二人將“愛奇”定格在《史記》記載九流末技,不純粹於儒家經義上,幷未指責《史記》之記載失實,流於怪異。《法言·君子》於“子長愛奇”條下又說:“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又以巫鼓。’”此條之解釋,歷來學者有歧義。李軌訓“不果”爲“不能”,“巫鼓”爲“妄說”,然不云“傳”作何解。至宋咸謂“非經謂之傳”,宋咸、吳祕皆以爲此條承上條而來,“傳”謂《淮南子》、《史記》,然皆未以“巫鼓”加之於《史記》。俞樾訓“果”爲“實”,汪榮寶取之,解爲“僅僅不實則亦已矣,又從而誣妄鼓扇焉,故其害爲尤甚也”,然不以“傳”承上條指《淮南子》、《史記》。是歷來《法言》注家未有以《史記》“愛奇”爲記載不實者。
揚雄之後,就“子長愛奇”進行討論的人很多,與揚雄時代距離愈近的人,愈頗不脫離揚雄原意。劉勰《文心雕龍·史傳》論《史記》說:“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此處“愛奇”與“反經”同列,猶《法言》“愛奇”與“愛義”對舉,所謂“愛奇”正是強調《史記》未將儒家道義作爲史料的去取標準。劉勰的論點來自班彪(叔皮)對《史記》的評論:“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觀班彪此論,可見劉勰對“愛奇”的理解與揚雄是一致的。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司馬貞《索隱》曰:“《呂氏春秋》云‘涵牛之鼎不可以烹鷄’,是牛鼎言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其愛奇之甚’。”皮錫瑞《師伏堂筆記》卷一論曰:“案‘牛鼎’即承百里飯牛、伊尹負鼎而言,《索隱》乃引《呂氏春秋》‘函牛之鼎’解之,反謂史公好奇,謬甚。”司馬貞未審上下文意,誤解典故,所引譙周之語,似乎意在說明司馬遷用僻典爲“愛奇”,已誤解“愛奇”之意。然譙周之意似幷不指此,乃指太史公爲鄒衍不軌之論開脫爲“愛奇之甚”。譙周所謂“愛奇”,亦似與“反經”同意,與揚雄之原意相去不遠。譙周與劉勰之說皆可以證成揚雄本意。
唐以後的學者在論及“愛奇”時,其理解開始有所偏移,大都着眼於《史記》取材的真實性,如劉知幾《史通·雜說》云:
且(揚)雄哂子長愛奇多雜,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當云《羽獵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譏之矣。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王本紀》,稱杜魄化而爲鵑,荊屍變而爲鱉,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
劉勰《文心雕龍·誇飾》談及“誇飾”的創作手法,認爲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人之賦作誇飾過分。劉知幾引此以譏揚雄亦愛奇,幷進一步說:辭賦之作愛奇亦無可厚非,但揚雄《蜀王本紀》乃史書,亦書望帝化鵑等事,則愛奇太過也。此處劉知幾是從史料真實性的角度來談“愛奇”的,曲解了揚雄“愛奇”說的本意,更何況據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指出,《蜀王本紀》作者有八家,又羼雜祝龜、燕胥等人之說,無稽之談多出於此二人之手,劉氏未曾深考,遂置喙其間,適增其謬。
宋代史學大興,董理前史者最大宗爲司馬光,頗注重考察史料之真實性,編纂《資治通鑑》的同時還撰成《資治通鑑考異》一書。其書卷一“上欲使太子擊黥布,太子客使呂釋之夜見呂后”條論商山四皓事云:
按高祖剛猛伉厲,非畏搢紳譏議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爲耳。若決意欲廢太子,立如意,不顧義理,以留侯之久故親信,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四叟實能柅其事,不過污高祖數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矰繳安施”乎?若四叟實能制高祖,使不敢廢太子,是留侯爲子立黨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爲此哉?此特辯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亦猶蘇秦約六國從,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魯仲連折新垣衍,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耳。凡此之類,皆非事實,司馬遷好奇多愛而采之,今皆不取。
司馬光對“愛奇”的理解完全從《史記》取材的真實性出發,他認爲司馬遷由於“愛奇”而收錄了很多“非事實”的資料,最後一句更是爲《考異》全書發凡起例,表明他對《史記》中類似資料的處理意見。其後晁公武對司馬光的做法加以表彰,《郡齋讀書志》卷五“《資治通鑑》”條說:
公武心好是書,學之有年矣。見其大抵不采俊偉卓異之說,如屈原懷沙自沈、四皓羽翼儲君、嚴光足加帝腹、姚崇十事開說之類,削去不錄,然後知公忠信有餘,蓋陋子長之愛奇也。
晁氏雖然贊同司馬光的做法,但他却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愛奇”的,他沒有懷疑這些史料的真實性,而是認爲這些事件“俊偉卓異”,對帝王的形象有損,應該本着“爲尊者諱”的原則加以刪削,所以他褒獎司馬光“忠信有餘”。他雖然誤解了司馬光,但是他對“愛奇”的理解却與揚雄本意相距不遠,可謂郢書燕說,歪打正着。
與司馬光同時的蘇轍作《古史》一書,其序稱司馬遷“爲人淺近而不學,疏略而輕信”,亦從史料真實性的角度提出批評,并根據《左傳》等書對《史記》進行補正,對其中荒誕不經處,加以删削。
其後又有金王若虛著《史記辨惑》,稱:“遷采摭異聞小說,習陋傳疑,無所不有。”其書列有《采摭之誤辨》、《取捨不當辨》、《議論不當辨》等專篇,直接指斥馬遷愛奇者有二,論《史記·魯世家》既載周公嘗請代武王之死,又載請代成王之死,有戾於《尚書·金縢》,認爲“戰國以來固已有此陋說,而子長愛奇,因以亂之耳”。此“愛奇”乃針對史料真實性而發。又論《史記·項羽本紀》舜目重瞳子事曰:
《項羽傳》贊云:“吾聞之周生,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陋哉此論!人之形貌容有偶相同者,羽出舜後千有餘年,而獨以此事遂疑其爲苗裔,不亦迂乎?商均,舜之親子,遺體在焉,然不聞其亦重瞳也,而千餘年之逺裔乃必重瞳耶?周生何人,所據何書,而上知古帝王之形貌?正復有據,亦非學者之所宜講也。夫舜以元德升聞,四嶽薦之,帝堯試之,上當天心,下允衆望,然後踐天子之位,其得之固有道矣,豈專以異相之故而暴興者哉?使舜果由此而興,則羽之成功亦應略等,奚其不旋踵而剿滅也?遷輕信愛奇,初不知道,故其謬妄每如此。
此條亦就史料真實性而發。其實馬遷乃傳疑之辭,未曾坐實,且此語意在比興,王氏不解文理,遂妄生議論。
與王若虛同時的魏了翁著《古今考》,專考漢史,注重辨別史料真僞,其卷二“拔劍斬蛇”條云:“老嫗夜哭,赤帝子殺白帝子,又恐是偽為神奇者之妄言。漢有偽《泰誓》三篇,出於河內女子,有周武王白魚入於王舟、火流王屋化為烏二事,後孔壁真《泰誓》出,乃不然。太史公好奇,怪聞異説,無不備載。有如白魚、火烏之事,出於僞書,則赤帝子之説無乃與之相似歟?”以史公好奇爲不辨史料真實性,對於僞書的材料也兼收幷蓄。
至明,楊慎亦事考據,《丹鉛餘錄》云:“玄鳥銜卵,……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蓐,燕不徙巢,何得云銜?即使銜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銜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奇之過。”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23《書留侯傳後》云:“史遷好奇,於《留侯傳》曰滄海君,曰力士,曰黃石公,曰赤松子,曰四皓,皆不著姓名,成其虛誕飄忽之文而已。溫公作《通鑑》刪之,宜哉宜哉!”梁玉繩《史記志疑》爲有清一代治《史記》之極有成就者,其書多引前人之論,於《史記》中不可信之說力辯其誣,尤於白魚赤烏(卷三)、拔劍斬蛇(卷六)、趙氏孤兒(卷二十三)、商山四皓(卷二十六)等說引爲史公愛奇之過。
在學者們指責司馬遷“愛奇”的同時,亦有爲司馬遷辯護的學者,但他們也是從史料真實性的角度來理解“愛奇”說的。如宋章如愚云:“紀,遷紀五帝,或以爲遷好奇之過,殆未深考。《五帝紀》多采之《大戴禮》《尚書》《孟子》,當漢初異端紛亂之時,而遷乃卓然有見於聖賢之餘論,其贊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又曰‘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此豈淺見之所能識哉?”《文獻通考》引周氏《涉筆》論《燕丹子》一書曰:“燕丹、荊軻事旣卓佹,傳記所載亦甚崛奇。今觀《燕丹子》三篇,與《史記》所載皆相合,似是《史記》事本也。然烏頭白,馬生角,機橋不發,《史記》則以怪誕削之。進金擲蛙,膾千里馬肝,截美人手,《史記》則以過當削之。聽琴姬,得隱語,《史記》則以徵所聞削之。司馬遷不獨文字雄深,至於識見高明,超出戰國以後。其書芟削百家誣謬,亦豈可勝計哉?今世祇謂太史公好奇,亦未然也。又如許由、伊尹、范蠡,亦多疑辭。惟信孔氏門人傳錄太過,如《五帝本紀》《孔子世家》,其間秕妄居多,是亦未能充其類也。”明沈長卿云:“史遷傳澹臺子羽,略其斬蛟投璧之勇;傳公冶長,泯其通鳥語之智;是天下最不好奇者也。說者曰太史公好奇,何所指?”清胡渭云:“《法言》病子長愛奇,而子長却不敢言《山海經》之所言。今人說河源,動輒引昆侖以證,是何其好學深思不逮子長遠甚,而愛奇獨過之也。”俞樾:“《五帝紀》曰‘擇其言尤雅者’,故唐虞二紀悉本《尚書》,高辛以上無稽,則略。而《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不以入史。至《高帝紀》,乃有劉媼夢龍、白帝化蛇之事,葢當時方以為受命之符,不可得而削也。世以史公為好奇,過矣。”以上各家均指出,太史公撰作《史記》,對史料已經有一番鑑別取捨的工夫,太史公不敢言者,後人多言之鑿鑿,故而不應指責太史公“愛奇”。論點雖與前舉司馬光等人不同,但對“愛奇”的理解却是一致的。
從以上觀點的羅列中可以看出,前人對於“愛奇”的理解分爲兩派,一是從史料的教化意義出發,一是從史料的真實性出發,前一種說法更符合揚雄的本意。 “愛奇”的具體表現也因爲兩種不同說法而有所差別。揚雄所謂“愛奇”,具體表現爲班彪所說的“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還包括譙周所說的鄒衍等非儒家學者的不軌之論,宋咸所說的“滑稽、日者、貨殖、遊俠、九流之技”,晁公武所說的“屈原懷沙自沈、四皓羽翼儲君”等有損帝王形象的事件。司馬光等所謂“愛奇”,則表現爲蘇秦約六國從,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魯仲連折新垣衍,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等縱橫家誇大之辭;又表現爲周公請代成王死、趙氏孤兒、高祖拔劍斬蛇、商山四皓翼立惠帝等傳聞陋說;又表現爲簡狄吞鳥卵、白魚火烏、滄海君、博浪沙力士、黃石公、赤松子等帶有神話色彩的災祥鬼神等內容。
事實既明,那麼,對揚雄此說的意義應如何評價呢?明朱國楨爲余文龍《史臠》所作序稱:“自愛義、愛奇之説興,而經史之辨始判。”頗能啓人深思。揚雄“愛奇”與“愛義”之辨,本旨在區別孔子與司馬遷,即區別《春秋》與《史記》。《太史公》在《漢書·藝文志》中屬六藝略《春秋》家,正表明在揚雄時代,經史未分,太史公撰史時以《春秋》爲標的,揚雄也以評判《春秋》的標準來評判《史記》。但《史記》實與《春秋》不同,有“愛奇”與“愛義”之別。“愛奇”者以博載爲功,故雜;“愛義”者以道義爲衡,故淳。揚雄敏銳地捕捉到了二者之間的不同,提出了“愛義”與“愛奇”之辨,將《史記》與《春秋》擺在了對立的位置上,同時也標明了自己的學術取嚮。揚雄的著作多仿效經典,但事實證明,“經”是時代産生的,不可復作,他仿效《周易》、《論語》而作的《太玄》、《法言》祇能歸入諸子一類。而太史公法《春秋》而作的《史記》也不是經,祇是未來史部的開端。揚雄雖失於自鑒,卻精于鑒人,“愛義”“愛奇”之辨,乃經史功能分化之端倪。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在目錄學中,史部漸漸從附屬於《春秋》的地位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部類,雖然客觀原因是因為史部書籍數量漸多,但經與史的功能分化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唐劉知幾雖仍列《春秋》爲史之一家,但更明確地指出了《春秋》與《史記》的功能性區別,《史通·六家》曰:“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曆數,籍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春秋》有褒貶黜陟,《史記》祇是整齊百家之言而已,無筆削,無微言大義,這也正是揚雄所謂的“愛義”與“愛奇”之別。可以說,經史的功能性差異,在揚雄已經提出,後人所論,衍其緒言而已。
雖然揚雄批評司馬遷“愛奇”,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司馬遷幷非不“愛義”。從取材的角度來看,史書當然要以博載爲功,但從司馬遷的個人思想來看,他同樣也自覺地尊孔子,法《春秋》,當然這一點在取材上、人物的次序升降上也是有所體現的。因此,“愛義”與“愛奇”不能完全對立起來看待。從思想上來分析的話,司馬遷學術淵源較雜,他雖以儒家思想爲主導,但還繼承有道家思想,對法家、名家、墨家、兵家、陰陽家也加以表彰;他對於歷史規律的考察,不僅注重從政治的角度去發掘,還注重從經濟、思想的角度去發掘,其歷史哲學思想也卓立於當時。他對傳統進行了充分的繼承和發展,他的思想是豐富的,多元多樣的,不拘囿於某家某派。而揚雄除了自覺尊儒以外,其時代距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已有較長時間,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逐漸鞏固,董仲舒等人建立起的哲學體系顯現出巨大的影響力,種種客觀條件促使他用更純粹的儒家的“義”作爲事物的衡量標準。所以從個人思想的角度講,由揚雄來評價司馬遷,當然是“駁雜”的。這既基於二人對儒家思想理解的差異,在對客觀歷史條件的分析中,我們也能找到原因。
唐宋以降,學者們對“愛奇”說的理解發生了偏移,又應如何評價呢?我們認爲,這也反映出人們史學觀念的與時俱進。《史記》以後,唐代以前,史書多出自私家撰述,史家需要從取材、思想上考慮“愛義”“愛奇”的問題。而唐代以後,史書多由官修,書出衆手,從表達思想角度講,在官方意識形態的控制下,撰述者表達個人思想的空間受到限制;從取材上講,史書詳錄史實的功能空前增強,形成了較爲固定的修史體例。劉知幾《史通》論史例而不論史意,正是這一現實的反映。這一現實抹殺了“義”的雜,“愛奇”說就無所指向了。但這一現實又促使史家轉向史料求真方面下功夫,到了宋代,有一批以徵實爲追求的學者,尤其是《資治通鑑》的編纂以及《資治通鑑攷異》的撰作,極大地推進了史學向着求真的方嚮發展,考據之學的興起與此當深有關係。這種風氣的興起不自覺地導致了人們對“愛奇”說的理解的偏移,這種偏移正體現了這種學術轉型的特點。對史料真實性的考證,將史料區別了等級,反映在目錄學上,可信度高的正統史書與可信度較低的雜史、野史、稗史的區分漸次嚴格,至於怪力亂神之等,則多被視作小說家言了。
文章的最後,我們再從史料真實性的角度來為太史公的“愛奇”作一辯護。司馬遷面對的是無人系統整理過的駁雜史料,其“厥協六藝經傳,整齊百家雜語”,誠如章如愚、胡渭、俞樾等所言,司馬遷已經有了一番別擇取捨之工,所謂“考信於六藝”,“折中於夫子”,“擇其言尤雅者”,“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不敢言之”;其不能定論者,則“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是《史記》有懷疑史料之真實性而仍然筆之於書者,蓋“疑以傳疑”之意也。但《史記》中還有很多荒誕不經如災祥鬼神一類,又該作何解釋?我們仍可以將《史記》與《左傳》類比來看。汪中說:“左氏所書,不專人事,其別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曰夢,‘其失也巫’,斯之謂與?”指出《左傳》也象《史記》一樣,多載荒誕不經之說。汪中又設問:“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僃書於策者,何也?”又設答:“此史之職也。其在《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屬春官,若馮相氏、保章氏、視祲,司天者也;大祝、喪祝、甸祝、司巫、宗人,司鬼神者也;大卜、卜師、龜人、菙氏、簭人,司卜筮者也;占夢,司夢者也:與五史皆同官。周之東遷,官失其守,而列國又不僃官,則史皆得而治之。其見於典籍者,曰瞽史、曰祝史、曰史巫、曰宗祝巫史、曰祝宗卜史,明乎其爲聯事也。”《漢書·藝文志》列數術略爲一大類,可見其在漢代爲專門之學,太史公《報任安書》也說“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可證當時史家本有記載災祥鬼神之職。明乎此,則可以無怪乎史公之“愛奇”矣。
(本文原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二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此次推送略去注釋,引用請依據原出處)